携手《环球》12年
文/顾功尧
编辑/马琼
从2013年上半年我在《环球》杂志发表第一篇游记算起,已过去整整12年了。今年是《环球》创刊45周年,而数字“12”也说得上是有些纪念意义的,因此有幸在此刻写下些文字,记录这些年与《环球》“携手”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。
我最初在《环球》杂志《行走》栏目发表的几篇文章,都是记述2013年元旦前后在土耳其的自驾游的点滴踪迹。当时每一篇文章都围绕一个地点或者区域,按照时间顺序先后撰写发表,可以说只是“一时一地”的记录。现在回望,这种方式的好处是时效性强,当时的真情实感和细节故事得以描摹得更加生动,但对于类似土耳其这样兼具厚重历史和繁杂地缘现状的目的地,又难免生出些片面或者肤浅的见解,留下了些许遗憾。
2014年初,我结束在法国巴黎的博士后学术研究,回国进入企业工作。因为工作需要,我经常需要短期甚至长期到国外出差,这也让我有机会延续当初海外留学时旅行的足迹。承蒙《环球》杂志编辑的赏识,又陆续在《街角》和《游斋》两个栏目发表了二十余篇风格各异的文章。
那之后,我开始尝试按主题将不同时间去过的不同地点串联在一起写。比如写冰川,我就把2013年游览法国勃朗峰、2017年乘直升机登上新西兰福克斯冰川和2018年徒步格鲁吉亚梅斯蒂亚小镇附近冰川的经历汇于一篇;又比如以音乐剧经典剧目《剧院魅影》这样特定的小视角小线索,去串联起巴黎、伦敦和纽约三座大都市的旅行经历,这些我盘算惦记了多年的腹稿,终于在《环球》杂志编辑的鼓励下得以实现。比起上面提到的“一时一地”的写法,我个人认为这是一种进步,或者至少对我个人在阅历和思考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
作为读者,我在全世界旅行的过程中也受益于《环球》的指引。闲暇时,我会拿起一本杂志仔细阅读其中的文章,即使是忙于工作或者在生活琐事间隙,我也会在线浏览近期《环球》杂志的文章目录,寻找灵感。差不多十年前,《环球》曾经刊登过一篇关于突尼斯撒哈拉沙漠中“火星营地”的游记,文章标题以及宛如外星球的图片,瞬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,令我惦记多年,并最终在时隔多年后我带着家人亲临其境,体验游玩。
在给予我充分自由、“天马行空”地串联组织素材之外,我必须感谢杂志社各位编辑朋友,还因为在我撰写发表游记的同时,编辑曾几次向我约稿,邀请我结合在海外学习工作的经历,写一写对国外前沿科技发展以及科研教学体制的体会。
这是在自发自愿写旅行笔记之外,杂志社给我布置的额外“作业”,然而我对于这样的任务也是欣然领受,因为这督促着我更加深入地去观察领悟一地甚至一国的方方面面,而我的日常工作原本就是关于科技创新的,完成这样的任务也有助于我更好地履行本职工作。
回望过去的12年,于我个人,用“携手”二字总结我与《环球》的关系还是颇为恰当的。这里面既包含着我一路走来、体验思考各国风土人情的旅行经历与思想提升,也帮助我围绕科技创新主题对世界加深观察。这两方面的原因,让我由衷地感谢《环球》杂志各位编辑,希望能够有机会继续携手,一路前行,共同成长。
(作者系北京中关村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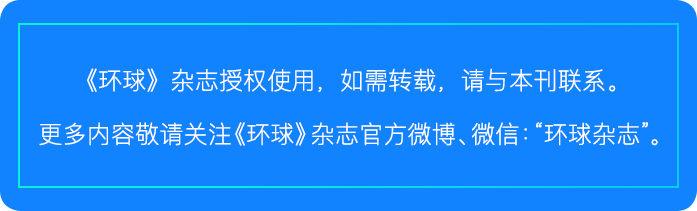

 手机版
手机版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