记录历史,定格瞬间
文/桂涛
编辑/胡艳芬
《环球》杂志1980年创刊时,我还没出生。不久前,我特意找来《环球》创刊号翻看,发现第一期关注的主题包括:伊朗变局中的中东博弈、英国阶层固化导致就业困境、美国青年对政治与投票失去兴趣、试管婴儿的奥秘、西德的国宴反映出的国民心态和民族情绪……当年《环球》驻外记者笔下,既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追问,更有充满温度的人文叙事;既有风雨雷电,也有柴米油盐。
这本创刊号向我描绘了一个陌生却又熟悉的世界。那些文字记录与探讨的阶层流动与固化、科技伦理、文明对话等议题,至今仍在叩击世界。这种奇妙的历史延续性,也从一个侧面彰显了《环球》选题的前瞻性和洞察力。
《环球》杂志的每一期都精准定格了特定时空下的世界图景,记录下那年那月这个世界上的人和事,记录下他们的情绪、立场、逻辑……当年记者笔下的“此时此刻”,已经是记录历史“彼时彼刻”的珍贵史料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《环球》杂志既是时代的速写本,又是历史的切片仪。每一期杂志都在为这个世界保留下一枚珍贵的历史切片,供后人调阅翻看。
那些在当时难以看清的现象、难以评判的观点,通过记者客观忠实的记录,都成为后人理解历史嬗变的“认知坐标”,供他们结合自己的时代分析和评判,来做出当下的选择。
很幸运,我也曾通过自己的采访记录、通过《环球》杂志这个平台,为制作这些历史切片做出过努力。我在非洲和英国驻外期间,为《环球》采写了近百篇报道——写过“文明交流互鉴中,中国能向非洲学什么”,写过“英国‘脱欧’这场反全球化的实验”,也写过英国菜为什么难吃,写过未来之城雄安如何体现中国人的未来观。
2016年起,我开始为《环球》撰写专栏文章,至今已近10年。
我觉得,很多驻外记者都和我一样,在一次次约稿和投稿中,深刻体会到《环球》的另一种价值——这本杂志不仅是历史的记录者,更是思想的锻造场。它帮助驻外记者将碎片化见闻淬炼成系统性的思考,不仅记录历史,更在塑造思考历史的方式。回头望时,这些思考已汇聚成一个记者几年驻外的收获与成长,沉淀为个人的眼光与笔力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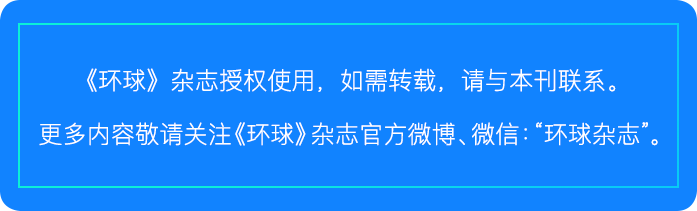

 手机版
手机版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