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与《环球》的20年
文/卞卓丹
编辑/吴美娜
2001年从仍处于内战中的非洲国家安哥拉回国后,我带着尚未抖尽的灰尘,第一次踏进了《环球》杂志的大门。未曾料想,这以后的20年,我的职业生涯会与《环球》杂志产生那么多奇妙而令人回味无穷的关联。
《环球》杂志编辑团队当年的主力军,是一群思维活跃、行动力强的年轻人。虽然杂志依旧是黑白版本,但其关注重点已经转移到国际时政话题。2001年最后一期封面报道《我为油狂》,成了《环球》黑白版本时代的收官之作。
《世界又远又近》是《环球》杂志2002年改彩后的第一期封面报道。由于预计到改彩后成本提升,售价上涨,会影响零售,因此我们对选题的要求更高,必须做到第一时间能抓住读者的眼球。改彩后三年多时间里,《环球》每一期的选题策划会气氛都特别热烈,要么大家一起“唇枪舌剑”,要么一位编辑“舌战群儒”,经常为一个标题或标题中一个字的使用争得面红耳赤。
2005年,《环球》杂志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。当时正是杂志策划思路的定型期。定型的成功,得益于编辑部的超前意识、不懈探索和勇敢尝试,而最具标志性意义的,是当年最后一期封面的年终报道。
那一年,西方媒体“中国威胁论”和对中国发展的“泛政治化”描述甚嚣尘上,《环球》杂志编辑部深感责任在肩,着手谋划怎样才能在年终报道中给出回应。同事们注意到,刚刚在热门综艺“超级女声”大赛中获胜的李宇春,被美国《时代》周刊描述为“颠覆中国传统”“对教条不屑一顾”的“叛逆偶像”。编辑部决定以此为切入口,拿出封面报道的体量进行反击。
编辑部派出记者专访了李宇春。读者从这篇题为《我不是<时代>说的那种叛逆偶像》的文章中,看到一个喜爱音乐、很酷也很温柔的单纯女大学生形象。除此之外,我们将当时西方媒体曲解中国的其他一些现象也罗列出来,组成一个完整的年终报道。杂志的封面设计也极用心——李宇春的头像和一本被“撕裂”的《时代》期刊,标题定为《被误读的中国》。这期杂志一经面世便被抢购,加印三次全部销售一空,创造了改彩之后《环球》杂志单期发行量的高峰,同时这组报道还获得新华社优秀作品策划奖,取得叫好又叫座的效果。
据此,我提出了《环球》杂志此后一段时间的基本策划思路——时政内核、时尚面孔。后来在报道中国公共外交成果时,编辑部选取了两位姚姓明星——姚明和姚晨,讲述他们通过篮球运动和公益行动让世界进一步了解中国的故事。封面标题《不一样的姚》非常巧妙地突出了中国公共外交的多样性。
作为国际报道刊物,《环球》杂志一直聚焦全球重大事件,并通过巧妙策划来报道事实、表达观点、传播理念。比如,在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出访或来访时,《环球》杂志推出“百问”系列,如《百问日本》《百问美国》《百问俄罗斯》,让读者通过100个与该国国情相关的问题,了解这些国家的基本状况及对华态度,从而认识到中国大国外交、周边外交战略的重要性。
又如,为了让读者了解走出去的现状和风险,《环球》推出报道领事保护工作的《护卫新时代“海外中国”》以及《海外留学40年》《海外风险预警地图》等特别策划。《环球》还通过“年度十大人物”“环球跨年汉字”“环球经济希望十国”等多种形式,表达对世界政经形势、年度重大事件和全球经济体发展趋势的观点和判断。
回顾21世纪前20年的《环球》杂志,那是一群心系国家、胸怀世界的年轻人,努力用自己的智慧和文字,让国人更了解世界,也让世界更了解中国,用信念和灵魂打造的一个适应全球化时代的“环球行走智库”。
(作者系《环球》杂志原执行总编辑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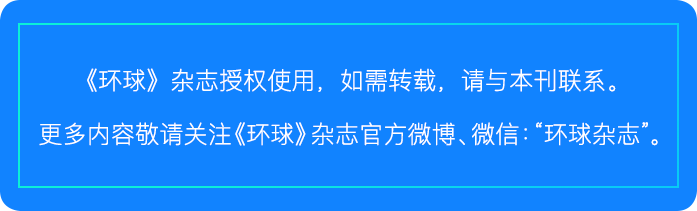

 手机版
手机版
